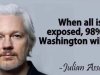哈维尔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表的看法,其实这比大部分东西方左派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要复杂,在更深的意义上,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识分子式的。但在我看来,仍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个以“非暴力抗争”而被世人广泛称道的典范,怎么会去领衔支持一场先发制人的侵入性战争呢?其实,哈维尔最根本的视角仍是基于捷克及东欧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蹂躏,和战后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经验。只是他复杂但精准的表述,在如此黑白分明的反战世界并未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2002年,在那场听众包括奥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nski)以及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三位皆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演说中,哈维尔回忆说,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一灾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捷克,影响到整个欧洲,而且祸延长久。第一次悲剧发生在上一世纪的三零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在德国慕尼黑对希特勒的野蛮要求让步(这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希特勒德国挥军占领捷克),这一历史悲剧让多数捷克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张,为什么要在邪恶一出现时,就必须先将其制止。
他接着说:“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经验,就是1968年被华沙公约集团的国家占领。那时候,整个国家重复述说‘主权’这个字,并谴责苏联的官方说法──宣称入侵乃是为了执行‘来自兄弟的协助’,是为了高于主权的社会主义理想,苏联宣称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胁,而全人类能够更早过上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胁。我们绝大多数捷克人都知道这是为了苏联对东欧的霸权、以及经济上的继续剥削,而不是为了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种说法,相信捷克的主权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占领捷克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这是我们经验到的第二个悲剧,它促使我必须采取异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衡量,在药剂师精密的天秤上衡量,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指伊拉克战争),是否真的是为了协助人类对抗一个邪恶政权,并保护人类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当然是比苏联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更为复杂的──‘来自兄弟国家的协助’。”
按照哈维尔的传记作者,也是哈维尔早年的好友约翰.肯尼(John Kenny)在《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一书中的说法,哈维尔的一生经历过六个时期:一、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早期学生时代;二、1960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捍卫“人道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human face)时期;四、成为异议份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随后的牢狱生涯时期;五、1989年捷克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六、最终的十三年总统时期。就像斯洛文尼亚批评家斯拉沃依·兹泽克(Slavij Zizek)所说:“沿着这一脉络,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许多弱点和怪癖的哈维尔,然而,这一切不但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失色,反而使他的业绩更具人性也更可感。”
此时,在哈维尔离任之后,我相信,应是他的第七个时期,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即哈维尔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后总统生涯”时期。我可以想像,此时的哈维尔,已深感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完的事情却有限。
无疑,哈维尔是一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他那毁誉参半的十三年总统生涯),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仅仅凭他秉持道德良知和深刻的思考写下的那些直面邪恶、深刻地启发并影响了极权国家异议份子思考和抗争方式的政冶文论:《生活在真实中》、《无权力者的权力》、《政治与良知》、一百四十多封《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的信等,便已足够奠定他在二十世纪人类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正因此,我们看到了没有产生哈维尔式人物的国家,如中国,当历史的机遇(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降临时,由于没有久经考验的反对及其运动灵魂人物,而无法促成历史巨变的不幸。中国没有广泛意义上的良心公民(少数的异议份子是不够的)和被他们内心真正认可的灵魂人物。中国的异议份子并不缺乏哈维尔式抗争的勇气,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力度也足够强烈,但我们缺乏哈维尔式的道德感召力和对于他人虚怀若谷的倾听,还有最重要的—–来自本性的反省、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能力,即真实地呈现自身的弱点,乃至由此而来的谦卑和不自信。中国的异议份子也缺乏哈维尔身上具有的那种与生俱来的童心未泯和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气质,那种面对别人批评时的不愠不火和彬彬有礼。
在哈维尔近年来的言论中,他并未掩饰对于自己的不满,我们再次看到一位试图重新回到“真实中生活”的哈维尔。他选择在“人权”领域协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动运动人士终结专制制度的工作,并认定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总统任期届满前,哈维尔在接受捷克报纸《民众日报》的采访中谈到,他本来只想做一个“造王者”(King Maker),没想到却阴错阳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做就是十三年。当记者再追问他,什么是他真正满意的生活时,他告诉记者,他最渴望的是回归到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写出新的著作是唯一可以让自己满意的事--这几乎是每一个曾经认真严肃并专心致意地有过作家生涯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的愿望。而哈维尔尽可能诚实地将它说出来了。
我以为,不是机遇,甚至,不仅是责任,而是命运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那也许是一个思想性特质的作家能干得更好、更具有独创性、甚至更适合的舞台。他不仅通过了苦难甚至死亡的考验,他也通过了政治权力对他的考验,即尽所有可能地在权力的使用上保持道德良知。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所有政治人物中的异数,一个虽有着传奇般的英雄业迹,却仍能保有思想品质的人。
一个简单的复杂人。

2013年10月5日,哈维尔77岁冥寿当天,贝岭特意前往布拉格郊区的哈维尔墓地,献上一束自郊外采集的野菊花,以表致意并默哀。(贝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