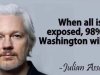【编者按】今天,2024年12月18日,哈维尔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的当天,贝岭发来他写哈维尔的一篇旧稿,给我留言说:“全球民主衰亡,威权逞狂,重温他非常必要。”在刘晓波的引荐和力促下,贝岭自1994年起尝试与哈维尔联系并寻求著作版权,成为六本哈维尔著作中文版的译者之一、编者和出版人,也是哈维尔的近距离接触者、温暖感受者及某些公开信的联署人,并自认是“(哈维尔)的文学和思想遗产的受益者与研究者”。此文写于哈维尔健在的时候,却也刚好处于贝岭准确观察到的“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即哈维尔告别政坛、回归一个世界公民的“后总统生涯”时期,也是几尽人生浮沉之后,最有积淀的时期。贝岭难得有机会跟哈维尔有多次接触和互动,可以带给中文世界第一手资料,呈现一个生动的具象的哈维尔。今天读来仍带着体温,如同这位富有感染力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仍生活在我们中间,启迪和守护我们。(言小义)
【题记】这篇长文写于哈维尔卸任捷克总统之后的2004年,那年底,他到访台湾。今天是2024年12月18日,哈维尔离开我们一晃已经13年。这十多年间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恐不是他所能预料的。假如他仍健在,思路仍旧敏捷,他对当下的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和加萨的残酷屠杀,尤其对全球民主的衰退,威权再起,仍至他念兹在兹的全球公民社会的挫败,以及他终生致力于的人权更偏向妇权及性别多元,作家及文学日益同温层化的现状,都应有他独到的见解。无疑,像他这样具有思考力的政治家已经罕有。所以,重温他的人生与思想遗产,可以让我们更为清醒地面对当下的世界。——贝岭
2003年1月下旬,寒风凛冽的布拉格,入夜后的市区灯光黯淡,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府的山顶布拉格城堡却灯火辉煌,那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哈维尔总统的卸任告别宴会,酒会上宾主尽欢、依依不舍,友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当了十三年总统的哈维尔正度过他最后的总统岁月。当年二月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美国作家大卫.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哈维尔的告别宴会的:
“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留影,接受人们的衷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扮出被牙医检查时惯有的鬼脸。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小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或你的肩膀,每个人都倾过身去听,每个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后合。”
无论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异议份子,或者一个“国王”,哈维尔都是难以归类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也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人,他是一个谦逊、腼腆的人,也是一个执倔固执、绝不认输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强韧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迹般的复原。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人特质,都在哈维尔身上呈现著,端看我们怎样审视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内心。而这一切,似乎都还远未终结。
哈维尔已成传奇,其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了戏剧性,假使将其喻成一场跌荡起伏的大战,戏码包括了成功的剧作家、勇敢的异议份子、哲人式的思想家、真正意义上的良心囚犯,直至连任十三年的总统。他的道德声望及对当今世界的无形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堪与圣雄甘地、教皇保罗二世(John Paul II)、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列。
而在中国,近十多年来,他那经由地下流传的(中译)政冶文论、书信、自传、访谈及其业迹,已使他在中国知识界和有形无形的反抗运动中成为精神的先知、勇气的象征与和平抗争的典范,而他最后被推选为总统的突然,也成为少数怀着野心或雄心的异议人士羡慕并试图仿效的榜样。
我本人曾有幸多次接触及近距离观察哈维尔,许多片刻确实是令人难忘的。
那正是哈维尔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的年头。1995年的春天,做为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受邀成为哈佛大学年度毕业典礼的主讲人,并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听众席前排座位上,面对坐在贵宾席上的哈维尔,得以不动声色地观察他。那是难得的几个小时,在冗长的,由当时的哈佛校长鲁丁斯坦(Neil RUDENSTINE)领衔的哈佛颂歌团队对哈维尔热情洋溢的轮番赞美中,我注意到哈维尔不时露出的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后来,我甚至看到带着反讽的不和谐,当讲台上川流不息的颂扬者用加重的语调滔滔不绝地向哈维尔和听众的耳膜轰炸时,他则心不在焉,自得其乐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尔还陷入沉思,当然,他面带感激,但这种场面此刻已无法让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时会被响起的掌声惊醒,随即警觉,并用警敏的眼神扫视眼前大片的“哈佛大众”。那一天,他用英语发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说〈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The Thin veneer of Glabal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而我在典礼结束后,冲上讲台,喊住他,和他握手,寒喧,但我们还未及多谈,便被他的安全保镖们隔开,挡掉,他抱歉地回过头来望着我,随后,在保镖们的挟裹下消失了。
1999整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过的,布拉格旧城区完全是一个游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弯的老石头街道内,仍旧有着强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后的巷子深处,处处传来捷克姑娘银铃般开朗的笑声,中间夹带着捷克男人略带压抑的低语,这美妙的噪音常常让由于人地两生,而守在友人公寓里端坐阅读的我难以自持,恨不得冲下楼去,堕入那笑声的深渊。我的朋友,汉学家,也兼任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布拉格办事处主任的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经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捷克民族喜欢‘投降’,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弱小,在强权面前,我们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所以,布拉格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幸存。”我想,他说的是对的,古迹和城市是无法移动的,人的肉体可以被征服,但人的内心不可能轻易被征服。也许,正是由于历史留下的这些失败感,捷克男人总是喜欢以匆匆进入捷克女人的温柔乡来麻痹自己。
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去逛逛,并顺便做一个访谈。被称为布拉格城堡(Pražský hrad)的总统府富丽堂皇,在助手的引导下,我拾级而上进入大厅,和想像中总统府应有的庄严肃穆颇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于由琳琅满目、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品和美丽的女性工作人员相映而成的梦境中,总统府墙壁上挂的大多是现代派的画作和艺术品,而行色匆匆的干练女助理们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击出的清脆哒哒声,在静静的总统府内回成一种令人心动的打击乐。
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带点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带惊诧,两眼发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离我数尺远的那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时,他用有点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释道,这是一位著名雕塑家送给哈维尔的礼物,因为巨大,哈维尔索性就放进了总统府的会客厅中,让他的客人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这令人血脉啧张的美丽金色尤物。在我面对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的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团(Rolling Stones)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我抬头看了一下金碧辉煌的大厅顶上硕大的枝形吊灯,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是滚石乐团这老哥儿几个(他们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维尔当了总统后,主动掏钱安装的,据说光线可以穿透总统府的石壁和窗户,投射到整个布拉格上空。这使得哈维尔有一阵一入夜,便拿着吊灯遥控器不停地把灯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又打开,兴奋得像一个顽皮的大儿童,搞得大厅内的秘书们被这晕炫的灯光刺激得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