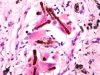前言
临近年关,劳动者讨薪的话题再次成为公众焦点。1月7日,大型连锁月子中心“爱家”猝然倒闭,旗下67家门店一夜之间关停,上千名月嫂走上讨薪之路;自1月13日起,200余名江西南昌建筑工人连续三日滞留城管局,只为讨回被拖欠的多达500万元巨额欠薪;1月20日,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员工因医院倒闭数月工资未发,选择以跳楼表达绝望……经济下行的危机如涟漪般扩散,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完全幸免;首当其冲的,依然是位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携带着2024年的无解难题步入2025年,正是劳动者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
如同绝大多数与劳动者相关的新闻一样,我们很难在国内媒体和平台上看到这些维权事件的详细报道,更难以得知事情最终如何收尾。事件被描述成偶发的、个别的,抗争的声音迅速被删除、遏制,是我们更熟悉的景象,而通报式后续也正成为一种常态。

2024年6月,冷藏车事件中,8名大龄女工在往返工作途中惨死运输车内,这一悲剧曾拨动大众心弦,引发舆论震动。在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官方将其定性为“企业未落实责任、驾驶员违法违规、属地监管不到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将问题归结为“驾驶员安全和法律意识淡薄”。最终,事件以驾驶员被批捕、涉事公司及相关行政人员被处理告终。而这起事故所暴露的村镇女性零工困境,再一次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
2024年11月,无锡职业学校学生无差别伤人致多人死亡,通报上蓝底白字的文字,则仅指认该学生“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书”“对实习工资不满”。随后,无锡法院在12月17日匆匆宣判其死刑,并在2025年1月20日执行。至此,事件以极其迅速的司法流程画上句号。他为何走向如此极端的道路?未见任何深度挖掘和反省。职校学生长期以来遭受的实习剥削、社会资源的缺失,亦在事件中被全盘省略。
然而,事件的全貌并非永远无法窥见。在耐心的追踪和梳理之后,那些被隐藏的真相终会浮现。本期年度特刊,我们选取了几类年度焦点事件——拼多多前员工反击竞业限制,比亚迪巴西工厂被控“奴隶劳动”,规培生以生命对抗“吃人”的制度,以及搬厂集体维权的实践,通过追踪和梳理,希望可以看见每一桩看似孤立的劳动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行业、社会乃至生产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拼多多前员工反击竞业限制
事件回顾
2024年过年前后,陆续有数位拼多多前员工爆料该公司滥用竞业协议的情况,引爆舆论热议。例如,微博网友“洋洋要活下去”自陈,其于2023年7月自拼多多离职,并拒签了为期6个月的竞业协议,但拼多多依旧给其发放竞业补偿金,并将竞业协议邮寄到家,使得竞业启用成为既定事实,继而通过跟踪偷拍等方式掌握其“违反竞业协议”的“证据”。2024年3月,拼多多向上海长宁仲裁委申请,要求该网友赔偿42.3万元。2024年4月28日,该网友发微博表示,拼多多只要自己返还1.5万的竞业补偿,就愿意撤回仲裁。不久后,该微博被平台删除。该网友并不打算就此和解姑息,决意继续进行诉讼,抵制拼多多的索赔。目前该案尚未有可信的进展。

又如微博网友“草娃故事”,其于2022年7月作为应届毕业生入职拼多多,8个月后离职,却被要求竞业9个月,后遭到拼多多索赔28万元;另一位拼多多前员工赵某则遭到了48万元的索赔,尽管他离职后进行了诸多个人隐私防护,却依然能被拼多多跟踪“取证”。2024年初,包括ta们二人在内的11位拼多多员工联名发文揭露拼多多滥用竞业协议的行为,其中最高索赔金额可达450万。据网友整理的信息,此时ta们的维权行动大部分仍处于一审阶段,个别尚在仲裁阶段的也难以指望获得有利于自己的仲裁结果。

进展与梳理
2024年3月21日,有多名律师表示愿意为拼多多的前员工们提供法律支持,在那之后并无更进一步的详细信息释出。由于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的匿名化处理,尚不能找到2024年内明文表述与拼多多竞业纠纷相关的记录。这些前员工的维权进展目前从网上很难了解到确切信息,舆论关注转移是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各平台也在对这些维权声音进行封堵,一些曾发声维权的前员工微博账号现已无从检索。
实际上,竞业限制纠纷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据2018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竞业限制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竞业限制纠纷案件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集中分布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劳动者上诉率明显高于一般劳动争议案件。2018年的这份报告同时指出,“竞业协议签订范围扩大”已成显著趋势;而竞业适用性、竞业关系的认定、违约金的合理区间等毫不意外是过去与现在共有的“老大难“问题。以江苏省公布的2015至2020年间226份竞业限制相关文书为样本,有统计表明,无论一审还是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竞业协议有效的比例都占据多数,且二审维持原判的比例也占据多数——由此管中窥豹,劳动者在竞业纠纷案中大多难以在一审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即使选择上诉也很难改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选择为拼多多前员工提供帮助的律师们会将这次维权视作“争取极度渺茫1%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拼多多滥用竞业协议的舆论爆发后两个多月,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就有关于“竞业限制协议不能限制非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的案例。该案中,一名推拿师离职后遭到竞业索赔,仲裁委与法院均不予支持,理由是该公司无法证实推拿师的保密义务,即竞业限制对该劳动者的适用性。然而,该案例的典型性对于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竞业来说,却是不典型的。“被竞业”的拼多多员工们面临的一大难点,正是在竞业限制的适用性上,ta们的工作内容并不像推拿师一样能够直观确认到涉密的可能性,而许多法院倾向于认为,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就负有保密义务。
工劳评论
竞业协议的本意旨在保护企业商业机密,但现实告诉我们,它作为对于劳动者的控制、威慑手段同样有效。正是因为竞业协议在实践中存在太多暧昧模糊的地带,使它能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竞业适用性的模糊)、有效性(竞业关系认定的模糊)、收益性(违约金合理区间模糊)的劳动控制手段。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包工、实习生等企业内的底层劳动力,以及如厨师、推拿师等在一般印象里完全和“机密”不相关的职业,居然也能成为竞业限制的对象。

面对竞业限制的无理要求,大部分求职者并没有太多选择,尤其是进入经济寒冬的今天,即使明知饵中有钩,仍有不少人只能一口咬下。部分法律从业者认为,竞业限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对其进行滥用的企业上。然而高达百万乃至千万的违约金,压在一个个如你我般普通的员工身上,这幅让人惊心动魄的图景很难不让人怀疑:在当前资方显著占优的劳资关系态势中,一个名义上客观合理的制度,不仅没有推动双方的均势化,反而愈发成为弱势方的重压,它真的如其声称的那样合理吗?竞业限制滥用的行为甚至算不上违法,用于劳动控制可谓无本万利;但劳动者一旦利用法律维权“频繁”,则会被扣以“恶意讨薪”。对于个别面临竞业限制的劳动者来说,或许有一些应对的经验,可以减少被原公司竞业索赔的概率,但问题的源头始终是那个让劳动者“别无选择”的劳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