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 谈谈林徽音在家庭之外,跟几个朋友(除了费慰梅以外几乎都是异性,没办法,当年的社会女子能受教育的实在不多,致使文人以男性为主。)之间的深重情谊。
沈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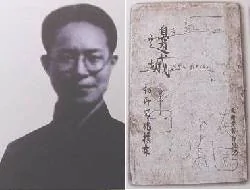
先从沈从文一桩小麻烦谈起。
沈从文在湘西的偏远山城长大,二十岁时受五四余波影响,奔赴北京,开始其文学生 涯,跟林徽音成了很好的朋友。
沈从文跟妻子坦白的表明他对北京一位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结果引起妻子的嫉 恨,他在徽音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跟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怎么可能不跟妻子说呢?他可以 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不只是家庭婚姻而已。
这件事让沈从文冲突茫然不知所措,便把痛苦告诉了林徽音,或许沈从文根本不知道 自己错在哪里。林徽音后来写信跟费慰梅说:「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这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的不 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情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这封信最后批评了当时左联支持的「普罗文学」,林 徽音看出「普罗文学理念」仅只是一种意识型态,而从文学中「人性是有其共通处的──不管阶层或生活背景是否有所不同」的角度而言,普罗文学才是好文学是没 有道理的。
林徽音这种体悟,当然是从沈从文跟她背景悬殊,却有类似的情感心境所得的体悟。 她那和沈从文共同的情感、心境,就是一种文学家艺术家的性格,概括来说,就是情感比家大,总会容纳进比家更多更多的人与事,与情感。最大,会大到让梁从诫 觉得:「我被母亲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凛然之气震动了。我第一次忽然觉得她好像不再是『妈妈』, 而变成了一个『别人』。」(这感觉发生于林徽音对日本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态度时)。(梁从诫「回忆我的母亲林徽音」)
爱比家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她跟某些性质相近的朋友之间常常久久深深厚厚的友谊。
徐志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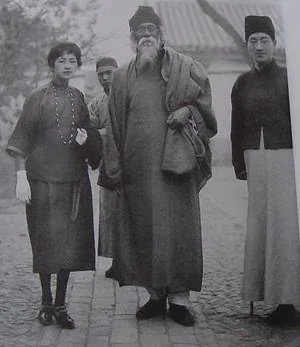
林徽音和徐志摩的爱情故事我不想多讲,我只想谈谈她和徐志摩升华后的友谊。
林徽音对胡适之说:「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 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的....我这几天思念他的很。」(1932.1.1 给适之的信)
1932.6,林徽音给适之的信再度提到志摩:「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哽咽牢套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 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
徐志摩死后,林徽音一直把他长存心中,不只从两篇悼念徐志摩的文字中可见,费慰 梅也如此印证:「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充 满激情的话,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音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响。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
费慰梅看的出来,那段男女情爱故事,林徽音已将之升华成知音知己,在她心中,永 远长存着两人的生动对话。
后来,在费慰梅的《回忆林徽音》一文中说:「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的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跟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 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 的这一空缺。」
林徽音这样的重情,继续发生在其他朋友之间。其中最感动我的,是患难知己老金。
老 金
当年在北平,「老金的小院子」正对着「太 太的客厅」,他们常常穿梭那扇门,从老金的小院子到老金客厅,或者从老金的小院子到太太的客厅。
老金跟梁思成林徽音一家关系是深 远流长的,逃难期间数度因为工作地点极近而一同跑路,梁思成为工作需要得离家在外,林徽音病重,也是老金在照顾他。梁思成说:「有老金照顾,我没有什么好 担心的!」而老金跟他们家情挚之深厚,孩子们甚至唤他「金爸爸」。
老金在长沙被炸梁思长林徽音逃向 昆明时,跟他们家各自星散,老金写信给费慰梅:「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后来他们在昆明重逢。老金跟慰梅 说:「徽音依然那么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采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语汇来形容她。....她不再有很 多机会滔滔不绝的讲话说笑....我们心中藏着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不止老金常提到林徽音,林徽音的 信中,老金也不时跃上舞台:「....思成笑着、鸵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 小食橱找点东西吃....。」「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 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 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梁家逃往李庄时,是林徽音最寂寞 的时期。因为这些对她而言是如此重要的朋友因为联大继续留在昆明的缘故,都跟他们分开了,当中当然包括老金。
不过,老金一休假就往李庄跑,所 以也出现三人联合写给费慰梅的幽默信件:「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作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 务。但杂七杂八的是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 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许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正常车站显的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他们因为物资堆 缺,纸张总是用到一点空位都没有。所以后面是老金的附言:「车站现在正在打字....。」然 后是梁思成的:「现在轮到车站说话:车站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 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耗损,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我的基础....。」 ─── 1941.8
这封幽默的信,充分将战时悲惨岁月、与人间患难亲情友情的双重主题赋格曲谱奏的有若天 籁。
老金本质上就跟林徽音一样,是个拥有在最沮丧绝望之刻,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 一春的性格的人。这是他们友谊常常久久的关键:两人性质类似。所以老金会对费慰梅说出他战时面对一无所有的人生哲学:「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
这就是老金,谱着跟林徽音近似的赋格,终生患难之交、知音知己。他在林徽音重病 到亡故这段时间,仍跃在林徽音笔下:「....老金染上那种集中营俘虏的野蛮习性....他的习惯是在自己 的窗台上放一只杯子和一双筷子,这样他每天早上可以用它们调一杯可可,有一次,他在房间里或尘封的窗台上找不到它们,气的不得了,后来我向他保证,今后我 会告诉女佣干脆别洗它们了,放在枕头下边让他容易找到!」
「太太的客厅」
林徽音重视艺文朋友当年就是鼎鼎有名的。她那「太太的客厅」,是个类似文艺沙龙 的地方,可以想象当时艺文人士交流聚会、观念冲撞,不时在这一方客厅里发生。当时的艺文界,诗的领域就有新月派与象征派这两大派别的争论;文学界左倾的人 标举的「普罗文学」──唯有中下阶层的生活面才有可歌可泣的高贵,也跟「艺术是用以表达人生」这人性共通论点互相别苗头。
林徽音认识的艺文人士不知凡几。
不过从书信中可看出,最后和梁思成林徽音一家有深交的,都属艺文人生观点比较近 似的那几个。林徽音对沈从文固然有「如此熟悉的感情」之叹,对老金何尝不是性质近似,所以她跟沈从文说:「你 一定得同老金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长沙轰炸时期,这些朋友仍常聚首。徽音对费慰梅说:「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附『国难』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 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作,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 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1937.11
一晃抗战八年,朋友陆续星散,胜利后林徽音重返昆明,与众老友重逢:「我们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 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但是那种使我们得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期的都更快的重建起来....即使谈话漫无边际, 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 代的诗人们在遭贬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其而遇时的那种欢乐,他们又会怎样的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 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 的苦与乐,其实是同一回事!」 ─── 1946.2
从当年「太太的客厅」这些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与现 在,到最终成为患难知己,一齐在各不同地方体验着最艰辛的中国历史与战乱生活,一齐变老了,而「信念如故,并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同一回事 ....」,我每每看过这段,想到老金、沈从文、萧干这些林徽音的患难之交,就深深的感动不已。
真正的艺术文学性情中人,情感一定比家庭能容纳的要多很多,其知音知交之情、乡 土家国之爱,也必然会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若要他圈地自限于小小家庭,简直是在扼杀他的灵魂。这种爱比家大的艺术性格,其实中外皆然。我非常喜 欢听古今中外各类知交相遇的故事,每每知交之遇的对谈纪录,再在让我神往。
而林徽音更让我动容的,是他们的知交早已走出「太太的客厅」,走出对话对谈,成 为彼此生命的见证;他们是「经历着对方的成长」,在生命体验中,各自坚持着该变的以及不该变的,最终却发现彼此有相同的坚持,以致于分散后重聚,仍是这么 的知心一如往昔,只是,比过往多了太多生命生活人性的深刻体会。「信念如故」,这是何等甘美的简要诠释。
人会随生活处境、环境变迁,心境观念都渐渐的改变;昔日情深知交,未必后日再聚首仍能相知相惜。我经过不知多少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几次戏剧性的 「曾为好友、最后形同陌路」,或「分散十多年,再聚首,竟彼此惊艳」;渐渐也明白知心实在可欲不可求,那「信念如故」的坚持,以歌德的话来说,就是:「朋 友相互间的一致,最初是出现在从事同样的工作爱好同样的事物,但是,让友谊长存的,还得有某些永恒的事物,诸如价值、信念与信仰。」....这在非战乱物 质丰富、生活琐碎平凡的时代,更是难能可贵。
我永远在心田深处记得我生命中曾是、以及现在正是的知心,那种深刻的分享,从思 想观念,到人性人生,到自我最深的渴望、软弱、欲求....我永远会记得这些知心在我生命中的陪伴与影响,并且会永远的珍藏怀念那种深深相契后的心灵悸 动!







